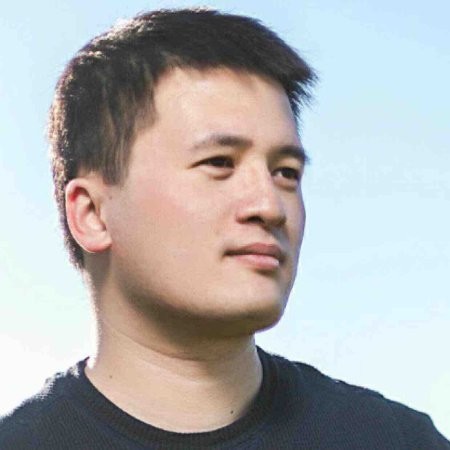论感谢
摘要: 本文讨论了感谢这件事的作用以及做好感谢所需要的能力。
开篇的话
我想动笔写这篇文章,原因来自于我自己设计制作“载歌在谷”志愿服务社区感谢系统的经历。
最初起草本文的时候,我正在和PP.W等几位志愿者伙伴们一起构建一个“载歌在谷”2019年春节晚会的志愿者感谢系统。这个感谢系统是受到谷歌内部的一个员工相互激励的系统的启发所作,我们称为”zgThanks”。这个“zgThanks”我们在2018年“载歌在谷”歌手赛志愿服务中首次推出,面临了很多挑战。2019年春晚启动之后,我们再次改进设计,并且更名为“好人墙”,虽然使用程度有所进步,但是依然处在很少被志愿者关注的境地。
我反思了一下之后觉得应该除了做好项目开发设计以外,也应该尝试跟大家分享我们设计这个系统的初衷。如果我们能够让大家理解为什么我们想做这样一个感谢系统,就能够更好地促进使用。
但是,也不仅仅是为了提高系统的使用,我最本源的初衷其实是想在一个志愿服务社区里面构建和倡导一种彼此感谢文化,并且跟其他志愿者们一起在志愿服务中修行提高我们感谢的能力。
感谢是什么
为了下文的描述方便,我们将施加感谢感谢的一方简称为“施谢人”,将被感谢的一方称为“受谢人”。我们将受谢人之所以被感谢的原因,其主动的行为,称为“佳举”。这里之所以要加以简称,是因为我们下面要大量在讨论中用到这几个被描述的对象,而笔者在现有的中文里面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对应词汇,所以也许这里使用了“施谢人”、“受谢人”,这两个听起来有点别扭的我臆造出来的新中文词汇。“佳举”这个次听起来可能用“善举”更加顺口,但是本文里想要概括更加广泛的“佳”而不仅仅是出发点(motiviation)方面的“善”的举措,所以使用了“佳举”这个词。
本文我们提到的感谢,是指在 施谢人 由于 受谢人 所做的 佳举 而对 受谢人 所表示的感谢。其中在时间关系上:感谢行为可能发生在 佳举 之后,也可能发生 佳举 之前。
广义的感谢,包括了被帮助人对施以帮助人的感谢,其他人对与一个做了好事儿的人的一种赞赏。由于很多时候一件好事的定义并不那么的确定,或者其获益人其实可能比较广泛,这些时候对某人的行为产生的积极效应的公开或者私下乃至默默的肯定,都算是一种本文语境下讨论的“感谢”的范畴。
感谢的作用——为什么要倡导感谢?
提到推广感谢文化,那么第一个回答大家的疑惑就是,为什么要进行感谢呢?我想,这是因为,感谢虽然常见,但是它的很多作用可能容易被习以为常所忽略。
感谢的第一个作用,也是最直接的作用,是让“被感谢的一方”感到开心。
感谢能够让感到自己的作品或者辛劳得到了别人的承认和肯定,感到自己的服务具有价值。
让我来解释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很多时候,人的沮丧、低落、抑郁,就是来自于得不到肯定,特别是得不到自己认为应得的肯定:学生在学校读书,考试成绩不佳,得不到考试结果为基础的自己对自己的肯定,也得不到亲友、家长、老师的肯定;员工在职场工作,长期的努力,徒劳无功,甚至取得的成果,被窃取到他人的名下;在亲情、友情或者爱情里,感到自己的付出不被认可、自己的努力不被看到、自己的心血不被体谅。许多人都发出过这种呐喊:“我付出了这么多,你怎么一点都看不到?”对个人如此,对组织也是如此。一个善于肯定的组织,一个赏罚分明的团队,比别的组织更有战斗力,更有归属感。
马斯洛的需求模型里面上面三层:人有爱与被爱的需求、被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些都是与感谢息息相关的,都是正确的感谢所能提供的。
感谢的第二个作用,是让“发出感谢的一方”,自己感到一种由衷的愉悦。
因为感谢别人的时候,对方是感动的,喜悦的。所以,油然而生地,发出感谢的人,会被对方的这种情绪所感染。哪怕有时候这种感谢并非当面感谢,通过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方式发送。即便无法见到对方的表情,发出感谢的人也常常能够因为想象对方收到感谢之后的喜悦,而感到一种因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而产生的满足感。
这种愉悦里更加高级一点儿的成分,来自于一种与对方共享成功的喜悦,当一个人能够感谢对方的时候,在潜意识里,也是在肯定自己作为这个感谢内容的一个目击者、一个关联方,自己也牵扯上了那么一点儿关系。顺便插一句,是否有这个“关联感”和“参与感”,是“感谢”和“祝贺”的最大区别之一。
感谢的第三个作用,是感谢的外溢效应。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感谢,将潜移默化的对感谢者、对被感谢者、乃至听到看到这个感谢行为的第三人,都起到一定的激励和引导作用。
感谢的本身是一种价值肯定。无论大小,感谢表明了发出者对接受者关于某一件接受者所做的事情或者所发挥的作用的一种感谢。进行一次感谢,将不仅传递喜悦,还将传递这种价值观。对与发出者来说,其通过感谢他人,而强化了自己对这种价值观的认可。被感谢的人,无论之前是否了解或者认可某一种价值观,当他被感谢的时候,也常常会读出其中的价值取向。无论接受与否,这种价值观被传递给了他一次。而对于其他旁观者、第三人,关注到感谢将不仅得到价值观的信息,往往也产生一种激励效应:原来,这样的行为会得到认可,我也要更多的做这样被认可的事情。
所以,感谢的人通过感谢这样一件事情,而让被感谢的人和外部观察者,都接收到了自己的价值观的输出,并且产生了一种下次继续的冲动。这是一种”正能量增加“的行为。从时间上(下次)和空间上(旁人),感谢的作用都将不止局限于感谢发生的那个时空的一点,而是会外溢出来。
感谢的第四个作用,是感谢其实是一种仪式,它会发挥在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方面的作用。
感谢中感谢的一方和被感谢的一方,在感谢之后,我比以前更信任你了,你也比以前更信任我了,而且我知道你比以前更信任我了,你也知道我比以前更信任你了,特别是如果有他人在场,有他人见证的情况下,它更是促进了这种信任的强化和情感和理智的“纽带(Bounding)”的作用。
第三人视角观察者两个人,无论第三人跟感谢者和被感谢者的关系敌我亲疏如何,只要这个第三人是客观的、这个感谢是诚挚的,都只能得到一个相同的答案:这两者感谢前后、关系更加紧密了。无论是口头的、发消息的、送礼物、还是甚至专门举办的一个宴会、大会,感谢构建了一种感谢者和被感谢者的一种共识。这就是一种存在在了解此事的人的脑海中一个“想象的共同”状态,这就是一种仪式达到的效果。
因为它可以为社会建构产生作用,促进信任,促进联系,降低摩擦和猜忌。感谢可以为双方彼此树立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威信,为彼此增加肯定,让彼此的关系更加稳健牢固——两个人、或者组织与个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有关系好的时候,也有关系不好的时候。当关系陷入低谷的时候,往日的彼此肯定,常常成为未来走出低谷,或者挽救关系、或者更上一层楼的力量。
也因为它可以为社会建构产生作用,如果一个人善于发现值得感谢人和事,将在自己的组织里积累出许多不同的人对他的信任和依赖,他的价值观将施加作用与更多不同的人,他的影响力,也就更大。
既然感谢有这么多好处,我们解答了为什么要感谢,那么怎样做好感谢呢?
感谢的能力——感谢其实来之不易
感谢也许是我们人类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受到的社会教育中的最早的一类了。从幼儿时代、会说话起,感谢就跻身了“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四大基本礼貌用语之列。似乎看来,感谢似乎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连小孩都不需要怎么学习就能轻易学会的。
可是,要做好“感谢”这件事儿,其实相当不容易。它需要 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一颗友善包容的心,以及强大的自尊心/自信(self-esteem),再加上一点技巧。
我不禁想到一句话郭德纲有一句名言:“相声这门艺术,台阶在门儿里面。”,感谢也如此,说出一句谢谢并不难,但是提高感谢的水平,却是无止境的。
就像谷歌给我的训练中有许多“life of a query”(搜索的技术概览)、“life of a dollar”(广告的技术概览)之类的,这类“life-of-a”为标题的课程着眼于用一个以时间轴为线索的方式来串讲和分析一个复杂系统。既然我们说感谢很复杂,让我们来用这个线索来解剖它。
让我们来假想这么一个场景:小明给在公交车上给孕妇让座,然后这个孕妇坐下之后给小明做了一个感谢。不仅如此,身边的
感谢作为一种能力的第一个要求是“发现能力”。
首先要有人发现这个善举。也就是说,作为发出感谢的人,首先要以某种方式观察到客观行为的发生,或者“可能的发生”。他需要对这个善举的“存在性”进行一个判断。
也许多数人会认为发现善举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不过其实,这恰恰是高级感谢的第一个门槛:看到别人所不容易察觉到的善举/辛劳。
巧的是,我本文写到这儿的时候,正好在一艘国际航班上。航班飞行时间很长,要跨过一个夜晚。我身边的空乘人员推着手推车正在我身边发放早餐,顺口说了一句:
I stayed up all night to pack the food.(我一晚上没睡,才把食物打包好)
我这才知道,一位空乘员为了给乘客准备热饭热菜,需要提前付出那么多的努力。
所以后来当这位乘务员轻松自若的时候推着手推车走到我的面前的时候,我很郑重地看着她说了声:Thanks a lot! (多谢!)。
可见,如果我们想要做到感谢别人感谢得很“到位”,需要我们了解别人所作的事情背后所需要仰赖的与众不同的额外辛劳或者特别技能。这种识别别人的努力与专长的能力,是一种“伯乐”之才。感谢的能力就像鉴赏能力一样,可以不断精进,可以无限广博,止于至善。
第二,做出感谢需要一种价值判断。
TODO
第三,感谢常常需要克服自己的ego,需要很强的self-esteeem才能走出舒适区,去感谢别人
TODO
第四,delivery 感谢本身需要一些技巧。
让人感到真诚
让人感到舒适
…
TODO
Meta
By Zainan Zhou, 2019-07-28 首次发表于 blog.zzn.im/p/appreciation
License: CC-BY-SHA-4.0
Worklog
- 2019-03 首次构思于Sunnyvale, CA
- 2019-05-14 撰写于捷克布拉格
- 2019-07-28 首次发表于Sunnyvale, CA
- Credit 来自 A.Z等的讨论与启发